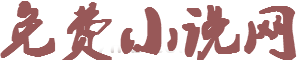第238章 将暗
作品:《冒姓琅琊》鸦啼影乱,暮天将暗。
偌大的荆州长史府内,只有刘寅一家五口外加几个奴婢,跪在中庭。台传御史张斌(朝廷派驻各郡督查钱谷的事务官,类于财政|部监管|局)带几队衙兵鱼贯而入,分列肃立。
沉沉暮色压下来,将众人的影子拖长,刘寅的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隐约听到身后家人强行压抑的啜泣声。
十二名台使仗身(钦差侍卫)身穿郁林白衣,腰间跨百炼钢刀,一字排开,身形如松;王揖站于阶上,手持黄麻诏书,冷漠的声音在这窒息的长史府中回荡开来:
“门下:
夫《春秋》诛意,礼所必惩;《月令》饬法,时无或纵。
荆州长史兼南郡太守刘寅,本卑门寒士,素乏操誉。
承时侥幸,遽秉要权。以斗筲之器,叨方州之任。
不思报效,反行苛酷。妄兴刑狱,滥逮士流。
凌轹经术之彦,三木横施;摧折清贯之望,五听俱废。
致使庠序辍诵,谤议腾于道路;仓廪废弛,怨嗟遍于闾阎。
岂非专擅福威,凌上虐下之验乎?
着即削其一应职守,黜留本州,补水曹参军之任。
主者告下,时速施行。
永明献很少保存诏文的完整格式(包括正文内容也常有缩略)《文馆词林》里的稍稍完整一些,而《文馆词林》中的所有南朝诏书都是以“门下”为题头的,而非两汉时期的“制诏”。《隋书·百官志》载陈朝发诏程序:“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所以诏书开头是门下。
当然,还有一种“中诏”的形式,是不经门下省的,以后会写到。
受近代西洋文学观的影响,谈到文学首先想到诗歌、戏剧、小说,似乎它们比其他门类更像“文学”(其实是更像近代英语世界中的iteratre)。这种视角延伸至关于诏令文体的文学研究中,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忽视诏令的文学性,造成严重的刻板印象,比如.....算了,例子太多又得罪人,不举了。
二是对诏令的研究限于什么比喻,什么壮阔,什么雄奇这种印象式的把握,停留在表面风格的层面,缺少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这就让研究沦为阅读欣赏类的“浮词”或者如教科书般“有结论、无思考”的文字。
其实重回六朝的历史语境中,诏令乃当之无愧的第一流文字。草诏者亦必臻一时之选,以第一流之文人作第一流之文字,岂非文学之盛事?(王融现在是中书侍郎,也是负责草诏的臣子之一)故中古文学极重之,《文心雕龙》、《文选》皆辟其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笔式》亦列其目。余嘉锡考《隋书经籍志》晋朝之诏令所著录凡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较唐大诏令多至三倍”,诏令于当时亦入集部,至《新唐书·艺文志》始转入史部,然犹未为定准。
《论衡》言“以文书御天下”,南朝则是“以诏令御天下”。这里并非指天子如何借助诏书对臣下发出命令,而是当面对半壁江山的正统危机时,在诏令文辞中维系住了王朝尊严与帝王法统。这是一个被文字所创造的世界,在指涉敌人的同时,也重新定义着自身,此种现实与理想的巨大沟通对于四到六世纪的草诏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必须用高超文学技艺在艺术规范与政治意图中寻找平衡,在威严与美辞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通过对语言元素做最大限度的运转安排,择取恰如其分的叙事策略,准确完成并不单一(很多情况下是复杂的)的表达意图,再现,或者说重塑一种事实。
这是具体可查的“文章经国”的案例。
文学研究者当具区别于史学研究者的独特技艺,主要着眼点不应在“写什么”,而应在“怎么写”。文学研究者当进行“重返现场式”的阅读,不仅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中古中国的读者,同时还要以作者的身份去思考下笔的其他可能性,从而判断草诏者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曾国藩言诏文“宜吞吐”(《曾国藩日记》),岑仲勉谓骈体制诏“易得含糊”(《隋唐史》),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是把这些“吞吐”和“含糊”说得清楚些。
什么繁缛、抒情、骈散、比拟这些文学要素简单罗列组成的有知识、无思想的介绍性论述实在益处不大。至于外围研究当然不会过时,但此是史家故物,非文学研究者所应专擅;文献研究依然重要,但在诏令领域,很难成为未来发展之希望所在。而更有可能“盘活全局”的研究范式是——以细读的方式,基于鲜明的问题导向,寻绎权力话语的文学表达与运作机制,探求诏令书写的实践策略与深层结构。
在这其中,文本措辞应该作为诏令研究范式中的学术定量,而对文本措辞的细读则是研究此定量的唯一有效手段。
好久没写长注了,因为没时间,今天正好多写点,再次重申,我加注都是改好每章正文之后才加的,所以有没有注对当章的正文长短都没影响。下两周会忙成狗,不过会尽力保持更新!亚古兽进化!!
本章已完成! 冒姓琅琊 最新章节第238章 将暗,网址:https://www.254y.com/430/430041/238.html